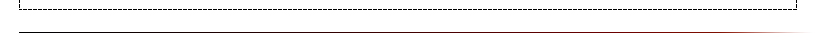陈子庄谈艺录
■陈滞冬编著《陈子庄谈艺录》
事绘画艺术要先有理论——所谓理性认识,然后再充分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不断否定旧我,这样才能逐渐达到艺术的高层次。
绘画,起初是描摹大自然,然后“生化”(即提高与创造)。生化的本领得自作者内心的修养,一个画家在艺术上成就的大小,就看其人修养之高低。
绘画须通“心灵”,须得“机趣”,此四字,论及者寡,能做到者更少。
我的绘画最大的特点是描写大自然的性格。在理论上,一幅创作是作者全人格、全生命力的表现,我努力想做到这一点。
绘画一道有两个要素,一是性灵,二是学问。无性灵不能驾驭笔墨,有学问才能表现思想。
必须于性灵中发挥笔墨,于学问中培养意境,两者是一内一外的修养功夫,笔墨技法是次要的东西,绘画光讲技法就空了。有人光讲意境,无学问来培养,则是句空话。然而如沈石田、文征明,学问虽好,但缺乏性灵,笔墨也会落空。八大、石涛有学问有性灵,可称双绝。性灵是根蒂。治学当治本,不应治末。
画画有两种境界,一是“画”,一是“写”,“画”是描画,“写”是表现,写胸中逸气。绘画艺术离不开“写”,但观古今画人之作,大多是“画”而不是“写”。
“我死之后,我的画定会光辉灿烂,那是不成问题的。”
“徐悲鸿的马过熟,都是那一匹,画穷了。”
“关山月画的梅花,像是从窗口看出去的景,等于照相机镜头的功能。画面有些像过去村姑剪纸梅花,一个方框框填满,无布局,无组织,无境界,无意趣,无动人的内容,无惊人的技能,不是内心先想一种情景再来画,而只是浓、淡两层点起就是了。无意境不能成一幅画。”
唐济民辑录《石壶论画录补》
对物写照,不论山水、人物、花鸟,均宜描写具象,个别特征,形质俱肖,不宜太抽象,普通泛泛为之,此为一定律。
大胆挥写,细心收拾,能得奇趣。
写意画,是在写字,不在画,要量寡而质高,写是写其意趣耳。
用色不宜多样,一幅之中青黄杂沓,失去韵致和朴实,华则易俗。色以辅笔墨,不可依靠色彩而惑人自惑。要色与墨两无碍,色有深浅明晦,以求色之变化,使山水增辉。
屡改者面貌,不变者精神。人工熔烁,技术尚焉,掇景发兴,胸臆尚焉。二者相济,方臻美备。
■李维毅辑录《石壶论画语录》
学画之法,初起时当弃其粗心,养其耐心,而能取形准确。若粗心未去,步法步骤,必失其真形,成之表面,久之落于形式,流为习俗,深入于心,难于救弃。反之,自矜其手腕明敏,心眼慧聪,一当动笔则弊端百出,而为终生之害,纵令老年知之,悔之固已晚矣。假使初学之时,有耐心去粗心,不求速效,从根基上下死工夫,笔笔到位,处处用心,看自己习作较诸别人,看别人之作证诸自己,何处为是,何处为非。
云林以渴笔取妍,余以湿笔取拙,昔人有云:“渴者清,湿者浊。”余以为宁拙浊而勿清妍,拙浊浑厚华滋,清妍浅薄枯窘。平淡萧洒,能意气宏调者为上,不如此不足以言笔墨之妙也。
破墨法与卧笔皴为古人所无,是我自创之法,对于西昌、西藏、茂汶等地山形恰到之皴,生等须当紧记。
染山水不宜用笔刷,只宜用笔点染或皴染,刷则使墨气有损,点、皴可以增其浑厚,亦无损于墨色也。
用色宜细心思考后方行,不可盲目乱作一通,用色不在多,而在于一色之中能有变化,有深浅明晦。一幅之中用色以助其山川之灵活,不当反而成为赘疣也,要色不碍墨,墨不碍色。
凡最高境界,不但在笔墨之内,而且要在笔墨之外。而意趣深厚,原不是依色量和墨量之多寡而定,然笔墨之内是有穷尽的,而笔墨之外是无穷尽的。
中国画为什么不叫风景画而叫山水画,是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故山为静,水为动,因之山水讲动静阴阳,而不叫风景画者在此。
画之雄强、超逸,能手而已;至于平淡、天真、无迹可寻,故曰淡然无极象而美从之。
文以达心,画以适性,适性而真画出焉。
古人忌用湿笔,以为湿则掩其笔锋。若能画大画用湿笔积水法,则层次深邃,韵味无穷。
■李维毅辑《石壶画跋选》
超诣之境,可望而不可及,远远招引好似相近,俱为由践之途。
——扇面山水
崚嶒兀岸中,自有秀逸之气,当于笔墨外求之。
——立轴山水
写蜀中山水,险峻易得,淡远至难。余去年游九顶山,燕子岩,南行百余里,群山万变莫测,惜老病之人,不能多行,归而默染此景,得一淡字。
——斗方山水《燕子岩》
取景虽佳而不能揉磨入细便是粗材,揉磨之功在于思者幽深而定。
——斗方山水《晨牧》
平淡天真,迹简而意远,为不易之境界也。余写虽未称意,而心向往之。
——四尺三开立轴《竹林水榭》
画种有声,不在笔墨而在意度,观者可以目闻也。
——斗方山水《秋兴》
蜀山玲珑巧峭,为难状之境,不明山意无从下手。
——斗方山水《蜀山图》
若妙合天趣自是一乐,不以天生活为法,徒穷纸上形似,终为俗品。
——斗方《芭蕉水鸟》
不读书,虽埋头作画,磨穿铁砚,断难得其仿佛也。
——题画
古之画梅者甚多,余独喜冬心、岳翁、白石之家。甲寅遇一凡斋中,问画梅法,因以牡丹红点之示范,工、拙非所计也。
——题小条幅《红梅》
孤融情景于一体,会句意于两得,其画自有妙境。
——题单条《柳杈翠鸟图》
多读书养成豪阔气度,东坡海上诗有云:“九死南荒吾不恨,奇峰幽绝冠平生。”能有此胸怀,其才智必有过人之处,学东坡当师其襟怀也。
——题山水画
多宝寺在彭州丹景山之巅,悬岩断壁皆生牡丹,苍干古藤,天矫寻丈,倒叶垂花,绚烂山谷,有丰碑书“唐时旧窠”四字,则知其事久矣。予曾到其地,故为图以记之。
——四尺中画《红牡丹》
吾蜀丹景山有祥云青花,大如碗口,开时绚烂夺目。
——四尺三开《绿牡丹》
吾蜀丹景山产牡丹,不在洛京下,余三十年前与盲禅师到此。今写白玉盘,能得其天趣。
——四尺中堂《白牡丹》
吾蜀天彭山中产牡丹,多从岩石间出,有墨牡丹一本,为世所罕见也,余三十年前见之,今写其意。
——立轴《墨牡丹》
彭州丹景山多宝寺前,有唐时牡丹,以状元红最佳,皆从岩间出。今写其意,为三十年前所见。
——四尺单条《牡丹——状元红》
青城后山金华庵,有牡丹色若丹砂,形似锦团,先花后叶,棠棣之花,翩其反而者,其或似也。
——题无叶牡丹《即枯枝牡丹》
彭州丹景山盛产牡丹,有唐时旧窠,高者八、九尺,而状元红风致飘逸,独得天趣,盖山中绝色也。
——题《蜀中牡丹——状元红》
疏或杂乱而无章,野或庸俗而少姿,当进之以清奇,作诗如此,画亦然。
——题《扇面山水》
吾蜀邛崃山,峰峦灵秀,谷中涧水清明见底,涧边多幽篁,密处遮蔽云天。余于壬寅之夏由平乐入山游,得数十稿,皆先后散失,今写此约略似之,用笔虽草草,自谓得其机趣,明眼当不以我为妄也。
——题《邛崃山水长卷》
邛崃山中有此甘溪,溪水清明,野禽常集于此,有玄天鹅甚罕见,余得此稿归来画黑天鹅。今又发箧见此甘溪图,并进写之以记游踪。
——题《邛崃山水甘溪图》
余年届六十,衰病交侵,无复幽兴,日理画课,惟极情乎郢匠之斧斤。勉成小幅八纸,奉寄作人先生求正,跫然足音,至希来诲。
——题《赠吴作人先生写生册》
不似之似才是真似,此语可以细味,有补于书画也。
——题扇《菊石图》
余久居蜀中,峨眉之秀、巫峡之险、剑山之雄、青城之幽常在心目中,每一落笔得其仿佛,具眼人能辨之。
——题山水
诗中冲淡惟陶元亮居其最,画之冲淡独倪云林得之。冲淡之境界、神韵、机格俱高,乃为涵养幽微所至,非力所能求也。
——甲辰题画语
庄子的艺术理论
庄子有没有一些对于声音方面的想法呢?事实上是有的。庄子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离开过艺术。在人类来讲,艺术就是眼睛的艺术跟耳朵的艺术,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家,是不可能离开对声音所做的艺术上的反省的。 庄子的哲学来源不能离开老子,不过,当老子获得他的哲理之后,他就印证在人类唯一的「政治生活」,尽管是打仗,而军事本来就是政治的延伸;老子从来没有拿人类第二种生活来印证他所获得的哲理,所以他是很集中的。因为他的立旨是那么集中,所以老子认为他应该已经把道理传达得很成功,这是老子的思想:「少则得,多则惑」。
庄子就相反了,庄子接受了老子所开创的那个哲理,这个哲理的特征、这个哲理一个很深入的特质,大概他都接受,可是却跟老子采取了一个完全对反的解释方向:庄子把老子所获得的哲理放在「全方位人类的心灵运作」方面。他好像不在乎那个哲理诠释得是否精准,他更在乎的是,他所获得的哲理是否能把他所爱好的心灵推动得够、把他的心灵开展得够,然后他的心灵在他的哲理指引之下、在他的哲理努力之下,向内来探索、也向外来探索。
我们在《老子》五千言里面我们得到的interpretation是:那个权力只有政治生活;可是我们在整本《庄子》里面,我们获得的是非常文明的、一种人性开展的多方面的生活。这个哲学个性差太远了,光是讲文字的运作就好了,老子的语言是维持最单纯的、存有跟语言直线的短路;庄子则不是,庄子的文字运作呢,他同时经历、同时包含了人类运用文字全部三种大的型态:
第一,哲理分析性的运作。不管是直接指向存有的、形上学语言的运作,或者反省我们认知能力的认识论的运作,乃至于专门在形式的严谨方面,类似逻辑概念推演的运作,庄子在这方面丰富得很、严谨得很、深入得很,例子太多了。还有第二种运作,就是文学的运作。他用语言的意向、语言的节奏、语言的感受,用语言的颜色、声音、动态、静态等等。第三种运作,根本在造型。所以哲学的运作、文学的运作以及艺术的运作,在整部《庄子》里面到处都充满了,他就用这三种语言来建构他从自己那个哲理所开展出来的、内在跟外在之间种种的收获。
我在这个地方一共有三个东西,三个东西里面,第一部分跟第二部分在整本《庄子》里面,非常精准地把庄子的艺术个性作一个很主要的刻画。当然关系到庄子艺术个性的章节多了,不过我作一个最精准的刻画,就这一个。
第一个部份提出一个字,这个字呢,是庄子自己表达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他认为最主要的一个特征;他用一个字来表达他自己整个人的精神状态的特征,就是一个字:「游」。
他用的是一个形象,他讲一个小小的故事——当然是他创作的故事,<在宥第十一>说有一个人叫云将,这是一个很好的政治领袖,他为了获得更高的政治能力,就自己出国了,把自己送到远处来获取知识。经过「扶摇之枝」,当他经过这样一个树林的时候,运气很好,碰到一位大仙叫做鸿蒙。
鸿蒙的意思是什么都没有开辟、什么都没有处理,树叶也没有剪、云雾也不开、野草跟青竹丝纠在一起、树叶又跟青蛙在打架,这么的一个鸿蒙。这个鸿蒙在干什么呢?就一个形象出现了:拍他的大腿,然后跳着来走路。这么一种高兴,比忘然还要厉害,就这么蹦蹦蹦的。那个傻瓜大仙正在高兴的时候,碰到了云将这个人,他就觉得很没趣了,「倘然止」,突然间停下来,「贽然立」,站在那边,晓得有人烦他了。于是云将一看到有那么一个怪老头,就请问他了:「老伯、老伯,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啊?」鸿蒙没有理他,还是拍着大腿蹦蹦跳,然后他说:「你问我在干什么?我告诉你『游』这个答案。」没有任何字,只给他一个字:「游」。
鸿蒙在干什么?他什么都不干——「游」,这个很重要,以「逍遥游」而言,用那么多的语言来作造形上的表达,更为集中。那个云将说:俺小皇帝呀「愿有问也」,希望向你请教,鸿蒙就看一看说:「吁」,被他累死、被他烦死了。云将说,我什么都搞好了,就是有个东西搞不过,什么呢?我搞不过老天。他说在我领导的那个地区里面呢,「天气不和」,九二一地震;「地气郁结」,又有八掌溪;「六气不调」,刚刚才有七级地震;「四时不节」,整天淹水,那怎么办?「今我愿合六气之精,以育群生,为之奈何?」「以育群生」这个问题一出来,那个鸿蒙就泄气透了,他又开始跳了,马上向前跳就掉头说:「我不知道不知道……。」才跳几下就跳到好远去了,比袋鼠还要厉害。
又过了三年,云将很勤劳,因为他又选上了,「过有宋之野」,跑到「有宋」这个地方,他这个人如果算紫微斗数,迁移宫绝对厉害,又碰到那个鸿蒙了——冤家的路永远很窄。「云将大喜」,上次问不到东西,马上跑上前说:「天忘朕耶?」大仙啊,你忘记小皇帝我了吗?「再拜稽首」,鸿蒙被他搞得只好回答他了,他怎么回答呢?继续前面那个问题。前面的问题最重要的是「以育群生」四个字,除了「以育群生」,其它大概都没问题了。碰到九二一、碰到八掌溪,你有什么办法呢?碰到地震?没办法的事情,「以育群生」的事情太大了。于是鸿蒙就回答说:我呢,「浮游不知所求」,我就一直生长、一直伸展,我的精神领域一直伸展、我的感性一直伸展,你问我要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但是我天天在伸展,快乐得很。
「猖狂」的意思是我很放开我自己,但是你问我去那里,我实在不知到去那里,我就一直去了——「不知所往」;最后那几个字才重要:「游者鞅掌以观无妄」,我就把自己整个投入、整个淹没在一个纷纷的现象里面,我沉默在全部的现象里面,我希望被我观察到一些不是现象变来变去的东西。「无妄」就是道家最重视的那一点所谓的「天机」,其实他就是在自己的五脏六腑里面打坐、在自己的灵脉里面做他的事情,所以他那个「游」是游什么呢?游乎生命的机密也好、游乎一切艺术的美也好,在庄子来讲,生命的机密如果能够发现,那么美对你而言是随手可得的;就像「庖丁解牛」,那个人是一个追求「道」的人,所以超过任何美的东西。
从这里面来看庄子的艺术个性,仍然是一种「玄德」的艺术个性。所谓「玄德」的艺术个性,是希望找寻一个真理,他认为当我们跟真理有直接的面对、并且可以跟真理往来的时候,那整个过程里面都充满了任何对美的掌握。所以在这个部分我所提出的、庄子自己给自己的整个精神风格的定位,就一个字:「游」。他把「游」摆在前面,虽然他最后提出一个「游者鞅掌以观无妄」,可是并不是只有这样子的,所以他前面先说「浮游不知所求 猖狂不知所往」,因为真理对他来讲是全方位的,这个是庄子的「游」。
这样的精神状态产生的音乐,绝对不同于儒家那种精神状态所产生的音乐,儒家的那种精神状态是符合「以育群生」的内在的。上次讲到《乐记》里面,怎么样把自己调整,然后声音出来了,反过来看看自己的感受,声音又出来了,又反过来看看自己的感受;考量一下那一些声音对我影响最大、那一路的声音对我的振动最久远,这样来「反情以合其志」,这样来让自己的内在能够符合「以育群生」。
所以云将所达到的那个内在,就是《乐记》里面「反情以合其志」那个内在;而鸿蒙所达到的,就是一个「游」。如果你再逼问他「以育群生」,他就跟你说,我要的跟「以育群生」不一样;我除了无目的是跟「以育群生」不一样,尽管是有目的,我也跟「以育群生」不一样。所以他是拿一个出世的道理来帮忙世间,不是拿一个世间规律来帮忙世间。
庄子知道他不是没帮忙的,但是他不是「生活规律的发现者」这样来帮忙世间,他是「出世间规律的创获者」来帮忙世间。这样子的一个思想在佛里面是非常具体、非常结实的,文殊菩萨所说的「大乘心定观净」就是讲这个道理,一个佛徒能不能够被批判说没有社会贡献?他说不是,只是佛徒所走的这条路,是只能是佛徒才能贡献的路。
这文章里面有两个地方:第一个,他不是「以育群生」这个目的规范之下的,他是无目的的;第二个,如果你一定要我交待一个目的,我是「以观无妄」这样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可以在两个层次上,讲庄子给自己内在人格在风格上的定位,一个就是无目的地跟真理的对话,另外一个就是把自己淹没、沉埋在一切现象里面,而希望有一个真真正正的究竟让他明白。这里面有个对应,就是「以育群生」,所以庄子让那个云将问问题问得很好。
第三个部份就是庄子表达一场声音。他以这一场声音作为一个比较完整的作品,直接讲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作品,以及在这个作品里面的人,是怎么样被影响的。这里面他比较重视的是在作品里面的人怎么样被影响,并且以能够这样子影响人,作为他认为艺术可贵的理由。见<庄子外篇天运第十四>。
一开始的时候,讲到一个人,他跟黄帝聊天。在《庄子》里面,尧、舜、禹、汤、文、武、孔子是仁德的代表,在内心的道德律里面找生活的规律;黄帝是一个玄德不怎么及格的一个代表——要加上这一句,黄帝在玄德上是一个不怎么及格的代表,至于最高,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他是玄德这一路的,是没有错的。
所以北门成就向玄德的中级班的黄帝请问一个事情,他说,你黄帝老兄在洞庭之野打开一个咸池乐谱——你看庄子是很仔细的一个人,我们听音响,音响的好坏其次,你先得有聆听空间——这个「咸池之乐」如果在室内来聆听,那就没听头了。他在那里呢?在「洞庭之野」张开他的「咸池之乐」。你看多厉害,一开始就踏入梅洛庞帝的身体哲学里面,讲求空间与艺术的关系。那个「乐」就在「洞庭之野」来展开。多仔细的一个脑袋!你要求古人这样子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信息那么多,希腊文化、欧洲十个八个思想体系都碰到了,总是有一些机会把自己推到一个立足点上面,产生一些视野,所以一碰到「张咸池之乐」,再碰到「于洞庭之野」,马上把空间跟艺术的关系连接起来,庄子也做到了,于是,他跟作品就往来了。
他说,当我在洞庭之野来听这个咸池的乐谱的时候,我一开始就感受到一种无来由的创造性。最重要的是这个无来由的创造性有一个经验:哇!它破坏了我任何任何的预期、他拿走我原先任何任何的经验。所以在艺术上,「创造」的意思是它出来了你才知道,它没有出来以前,你想都想不到!这个「惧」是创造性被打击到的时候,一种心里面的反应:「始闻之惧」,感受到创造力的不可预测;「复闻之殆」。再来,被这个作品的艺术能量压迫、渗透,最后整个艺术品那个大的能量压在他身上,他开始感觉到沉重,沉重到自己承受到虚脱,然后产生一种好像蛇脱了皮的感觉。所以创造力的感受、创造性的感受,到一种能量带来的沉重感,沉重感带来一种精神近乎虚脱感,这个是「殆」的意思;「卒闻之」,听完了,「而惑」,动摇起来。我动摇起来,完整的精神变成一种恍惚,恍惚的时候动动荡荡,然后精神开始沉静了,「乃不自得」,怎么我交出了自我?「不自得」是我怎么交出了自我?
所以你看,所有好的艺术、够力量的艺术进入人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创造性,再来一个大能量,最后让你交出了自我。完全不一样的艺术滋味!
这三个特征先摆在前面,后来整篇都在讲这三个东西。所以黄帝听到以后,先赞他一句:「汝殆其然哉」,这个意思用今天的白话翻译就是:哇赛!你好像听对了喔,奇怪!「吾奏之以人 征之以天 行之以礼义 建之以太清」,他说我一开始的时候,还是一样从喜怒哀乐开始,然后以声音上的旋律来进行,「征之以天」的「征」是「以它作为指引」的意思,跟着天的指引,「天」就是对象舒舒服服本来的那种样子,就是声音它本来的一个规律,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旋律了;还是喜怒哀乐啊:「奏之以人」,还是旋律阿,然后呢,还是离不开文明:「行之以理义」那就是文明的内涵,喜怒哀乐里面文明的内涵就是爱情、就是想象力、就是观心……;最后,「建之以太清」,我以一个没有什么样混浊东西的自己作为建立,「太清」的意思其实是我尽量符合作为一个空架子,不干扰。好,这是一个大略上的表达,其它的旋律、文明的内容,最后以一种接近于「无」的道理来使它们能够成为一个作品。「太清」就是接近无的一个道理。
「夫至乐者」,他说音乐这个作品到了一定的程度,「先应之以人事」,这就是「奏之以人」;「顺之以天理」就是符合旋律,不能够不顾旋律,音阶是音阶、音程是音程,时间的艺术是以时间作为形式的一种艺术;「行之以五德」是我们这一个地区、我们这一个族群所选择的文人的内涵,「五德」里面到底讲的是什么不重要,就是任何一个地区、任何一个族群,它总会在一切内涵里面,选取一些它选取的内涵——在中国来讲就是「五德」,仁义礼智信也好、金木水火土也好,没有关系;然后以这个作为根本,「应之以自然」,把它丢到天地里面去,天地的自然推展出来的事实,好像要把它作一个调理、作一个处理;「太和万物」的「太和」作动词用,它使得一切的内容、一切的节目有一种太和性,它不只是一个整体,而且是有一个滋味的整体。
「四时迭起」,这里面讲两个东西,一个是气氛,一个是细节。细节就是音符,气氛就是音符与音符之间产生的、一种音符以外的 feeling。「太和万物」就是音符以外的feeling,「四时迭起」就是句子、就是音符,「万物循生」;然后「一盛一衰」,音乐就是强弱嘛、就是短长嘛;「文武伦经 一清一浊 阴阳调合」,庄子是一个有听力的人,他自然会感受到音乐成于强弱、快慢、深浅跟唱诸如此类的,所以一个一个的「阴阳调和 流光其声 蛰虫始作」,于是慢慢地,细节上来了;「吾惊之以雷霆 其卒无尾 其始无首 一死一生 一偾一起」,注意他在进行中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音乐大概就是这样;「所常无穷」,这就是创造了, 你从前面几个句子,恐怕不能预想到后面几个句子;你从前面的进行,预想不到后面的进行——「所常无穷」。
我告诉你,在我听古典音乐这个可怜的经验里面,只有莫扎特让我感觉到「所藏无穷」,他的声音就是那么从天洒下来的,就好像一个投手没有预备动作那样,最厉害的投手,预备动作是最轻松的。「所常无穷」是说那个声音应该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一不可待」,全部破坏掉你任何的预期,那个创造力——「一」,是你预期不了的,所以「汝故惧也」,你就被惊吓到了:「耶,我怎么都没想到?!」好,这就是第一个经验,第一个经验就是创造性的反射。
第二个经验来了,那个艺术能量来了:「吾又奏之以阴阳之和 烛之以日月之明」,不要以为他是死死板板的喔,音乐离不开强弱跟快慢:「能短能长 能柔能刚 变化其一 不主故常」,「变化其一」跟「不主故常」是相反的。「变化其一」:音乐是准确的;「不主故常」的意思指音乐世界的诞生,是从你没办法预估的创造性来的。好了,能量的形容词来了:「在谷满谷 在坑满坑」——我们现在天天在说「满坑满谷」,是从《庄子》来的——,那个音乐能量是渗透性的、慢慢地占满的,山谷就填满它、坑就填满它;「涂隙守神」,「涂」就是「杜」的意思、塞满的意思,每一个我们感觉的缝缝它都塞满。「守」是张力的意思,「神」是一种领略。塞满全部的缝缝,然后我们在感受上有一种很大的张力,就站在那边,好像守卫什么一样;「以物为量」,我们的心能够接受多少的声量,就像画画一样,颜色也是在我们视觉的量里面。「以物为量」是说它的艺术能量大到几乎是我们接受的生长的一个尽头。
「其声挥绰 其名高明」,「挥绰」的意思就等于说是韵的悠扬;「其名高明」的「名」就是节奏,明显的节奏,非常的高明。它的韵非常的悠扬,它的节奏又非常的断然;「是故鬼神守其幽 日月星辰行其纪」,不管讲到感觉、不管讲到宇宙,都能够跑到它比较难到的地方;「吾止之于有穷」:一句还是一句、一章还是一章、停顿还是停顿,音乐没有不停顿的,可是当它停顿的时候,音乐的张力、音乐的活动「流之于无止」,你不会因为这里面我用了休止符,你就感觉音乐已经停了。「止之于有穷」可以领略为里面随时有休止符,可是音乐的张力、音乐的渗透力是没停过的。
「子欲虑之而不能知也 望之而不能见也 逐之而不能及也」,这个就是艺术超过我们一般的精神运作。你拿思考来想它,你想不到的,这是创作;你希望用感观直接地去看到它,你看不到;你就用你的心意、感情去追逐它,你追逐不到。然后「傥然立于四虚之道」,你全部都挨打了,因为那个创作是那么样地丰富,可是没有一个东西是你想象得出来的。你看这多厉害,那么大的一个艺术能量,可是没有一个东西是在你预期里面的。于是你自己很空虚了、你自己被掏光了,「倚于槁梧而吟」,你变成靠在梧桐木上,发出了很自然的、听音乐而来的、你自己内在的和声,听得高兴的时候你就咿咿喔喔。「倚于槁梧而吟」应该是演奏的那个人弹琴「倚于槁梧而吟」,那听的那个人靠在树上发出声音也可以说是「倚于槁梧而吟」。
「目知穷乎所欲见」,你直接的感官没用了;「力屈乎所欲逐」,你追不到它;「吾既不及已夫」,我没办法了;「形充空虚」就是说被艺术充击过来,艺术能量愈大,我愈是有虚脱的感觉,我整个形躯所充满的就是没有、就是虚脱;「乃至委蛇」,好像蛇再蜕一层皮;「汝委蛇」,那种沉重感、那种量感的冲击之下「故怠」,所以你感觉到受不了了。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 调之以自然之命 故若混逐丛生」,「混逐丛生」就是突然来了一大堆散板;「林乐而无形」,「林」就是总总,「乐」是美妙的音符,「无形」:它不是个旋律。你注意喔,「混逐丛生 林乐而无形」,它已经脱离旋律了!我又想到莫扎特的音乐,他有很多「混逐丛生 林乐无形」的音乐。
「布挥而不曳 幽昏而无声 动于无方 居于窈冥」,那个时后音乐的进行,不是以明显的量感来进行,而是以听觉的希少、可是音乐能力那一种难以形状来进行。用白话来讲就是微弱,愈微弱的时候,音乐的能量可能愈强。它不是那一种可听觉的强壮,它是指在那个时候,音符不见得怎么样,可是有另外一种力量;「或谓之死 或谓之生」,它不是那么样强壮的,几乎在活动不活动、存在不存在、有神采与无神采之间、有旋律与无旋律之间;「或谓之实 或谓之荣」,有时候感觉是果实,有时候感受是花香;「行流散佚 不主常声」,始终离不开一个创造力。
「行流散佚」也是一样,「不主常声」,没办法抓住它的伟大;「世疑之 稽于圣人 圣人也者 达于情而遂于命也」,「达于情」是一个真实——古人常用「情」这个字眼来代替真实,尤其在儒家里面,儒家的经典没有「真」这个字。以前有很多外国学生都问我:整个儒家都没有「真」这个字,一个哲学体系如果没有「真」这个字眼,怎么能是一个哲学体系?我说:有啦!它不用「真」这个字眼,儒家用「情、信、实、诚」那一类来讲「真」——「达于情」就是达于真的意思;「遂于命」的「命」是限制的意思,「达于情」,通达于真实,然后实现在一个限制里面。限制就是一个实现,有了限制才是实现。
「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它里面最深入的那种生命天机并没有非常显露,「而五官皆备」,可是你感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人,没有一点点不够;「此谓之天乐」,这个就是天乐。徐元白的声音颇有一点「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你仔细听,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很清楚,有音程、有音阶、也有旋律——「五官皆备」,可是他就能够出现比散板还要散板,这个「天机不张而五官皆备」;「此之谓天乐」,天乐怎么样呢?「无言而心悦」,说不出话来,不要去形容,可是很高兴。「故有焱氏为之颂曰 听之不闻其声 视之不见其形 充满天地 苞裹六极 汝欲听之而无接焉」,你感受到有一些一直影响你的,你希望具体地、明白地听出,到底它那里影响你,但就是它影响你的地方是你听不到的,于是你慢慢地就动摇了,慢慢地就好像交出了自我。
最后来一个总结:「乐也者 始于惧」,没有创造力,什么都谈不上。在艺术方面我就是比较强烈的「创造论」者,我一听到习惯,就没什么兴趣,一看到这个东西是别人来的,就没什么兴趣。所以「始于惧」,你一定要有一种surprise,有一种第一次碰到这个东西时的惊讶;「惧故祟」,「祟」是莫测的意思、是鬼怪的意思、是好玩的意思,是那个艺术的兴趣,要不然有什么好玩?好了,这么一场的丰富,接下来要有创造力,这个创造力又要跟着足够的能量,所以量感是艺术品很需要讲究的;「又次之以殆 殆故遁」,那个量感打击下来,你就溜了,可它追着你;「卒之于惑」,你最后动摇起来、恍惚起来、宁静起来,最后交出了自我,于是你就没意见了——没意见是很难的:「惑故愚」,就愚笨了,愚笨比较接近那个真实,当你整个人与真实接近的时候,真理就在空气里面带着你出国:「载而与之俱也」,带着你去游了——最后还是回到庄子的艺术精神「游」,「道可载而与之俱也」,「道」跟你一起「拊髀雀跃」。
儒与道的艺术观
道家是相反。道家一开始的时后,是一种直觉的美,一张开眼睛就被那个美完全吸引了,被那个美吸引了之后,他自己都忘记自己了,装满了是那个美。再往后,道家找到一个的「玄」。没有找到幽深的「玄」的道是浅的,所以像何晏、王弼那种玄是浅浅的玄,是一个清谈,不能够称得上是道家的人物,除非有一个幽深的玄从自己里面发现,那就可以了。所以这一路讲来是一个personality的路,personality就是西洋讲的位格。那个「位」是从神来的,而我们把神变成一个形而上的真理、把祂变成一个普遍的真理,把祂变成真理,自己就没有关系了。没有真理的赋予,那个person是不成为person的。回到刚刚讲的那个儒家,那是从moral sense 、从那个道德感上升到morality—道德性。可是就儒家所领略的道德性是在那个「伴」里面,所谓的「伴」到后来由于种种的缘故,在伴里面的血缘性被放进去,这个时候就复杂了。如果是就血缘性来讲那个「伴」是一种;如果可以在血缘来讲、也可以超越那个血缘性来讲,那是另外一个滋味。
真正去感动一个儒家他这个滋味跟那个滋味的,是在「值得」那个地方去检证,看看这个「值得」里面包涵多少血缘方面的成份。如果在这个地方,血源过头了,那是一种情况,血缘过头在儒家不见得不对。孔子说,老爸偷了羊,我替他隐瞒,那是对的。那孟子被逼着说,有一天舜做了天子,要陈定南男当最高法官,可是舜他的老爹杀人了,怎么办?孟子说,他就毁掉自己来负担这个血缘的「值得」。在这个地方有很大的人性场景可以开辟,不见得不对,这是一种选择,在这个地方是很尖锐的。
就道家来讲,那一个深入的地方不是血源的感动、也不是广大人类事业那种责任的感动,而是内在来自存有的讯息,所以就是personality。在哲学方面最大的错误,就是冒冒然地把morality画三条杠杠全等于personality,这是不对的。在西方,不管morality怎么样高明,要跟personality画等号是不可能的,因为personality是一种人,morality是另一种人。我们说佛跟老子、庄子都接近personality,来自存有的讯息是他人格最大最大的一个来源;就儒家而言,是我永远在可意识这个地方,坚持一个值得不值得,那是最高的判准。
所以就儒家来讲,「心」是最高的裁判;就道家来讲,「玄」是最高的一个教诲。所以道家开始的时后是在直觉上的一个美,这个美带着很大的惊讶、带着一个很大的对大自然的羡慕、很大的一个他对大自然的享受、他的惊讶、他的好奇、他的了解等等各方面,然后从直觉的美到幽深的玄往来一番以后,就产生一种几乎是全方位的局面,他这个全方位的局面是丰富的、是广阔的,就是一种力量、就是一种变化。最后道家投入在一种创新里面,道家创新的极致就是生与死。在整个全方面的局面里面,他碰到丰富、广大,碰到力量、变化,他碰到以生跟死来推出来的「心」,这个地方是一个直觉的美、幽深的玄跟一个全方位的局面。
道家的精神如果用中文的语汇来描绘,叫作一种忘我的「游」,「逍遥游」的「游」。游在直觉的美上、游在幽深的玄上、游在全方位的局面上。基本上,他在忘我里面建设了我,然后在「游」这种生命形态里面,与真理之间不相亏欠,真理融到他里面,而他以一个人来代表真理,最后,也是道家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人是真理的载体,这是道家的极限,就是这个人作为真理的载体。这跟儒家的感情的、永远都是一个我、一个伴,是不一样的。
你从《老子》、《庄子》的气氛看下去,忘我而游。庄子一辈子使用「游」这个观点所打开的思想相当相当可观,所以我暂时以庄子做为一个道的一个神态、一个真理的载体。
「游」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精神领域的扩展、生命形态的扩展、不被肉体的粗渣障碍的一个神奇的认知与一个神奇的力量。不被肉体粗渣所障碍这个观念,在道里面是很重要的,如果基本上你全部被肉体的粗渣所障碍,谈道家谈一半可以,谈上去就不行了,因为肉体的粗渣对你造成那么多的障碍,那么你还要用人来承载真理?承载不了什么!这个地方跟佛就有一个接轨,但是佛在这个地方产生一种宗教的悲悯,然后让「作为真理载体」这个办法能够由一个教团在世间作一个给予性的工作。这种宗教的悲悯在佛来讲是很够,可是在道家我们看不出来。孔子建立他的教团、释迦牟尼建立他的教团;可是老子没有建立教团,因为他不要伴,庄子也没有建立教团。
所以就我在经典上所感受到的,到底「伴」对你是不是绝对的?如果是,大概是儒家一路。儒家不在乎眼耳鼻舌身意那个生命的粗渣造成的任何障碍,他不管这些;在道家,他有一种来自存有的信息,他要存有信息的告知是一个完整的告知。「孔德之容,唯道之从」,就是真正能够达到「空」这种内在,这种内在必然是走着「道」的步伐,「唯道是从」就是他整个是「道」的步伐。只要你的内在达到如同虚无、如同空,那个粗渣再也不妨碍你了,那么你就进入「道」的步伐,这就是「孔德之容,唯道是从」,这个时候是没有伴的。
儒家从来都不是这样子的,他最重要的是整天检查自己是不是一个值得生活的人,甚至在这个逻辑之下来讲,他家里的摆设是不是选一些值得摆设的摆设?这个动作是不是值得的动作?儒家处处都有一种同时的自反、同时的反身。在他一个动作出去的时候,对这个动作同时有一个反身的评价:这是不是值得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值得」是准备在面对「伴」的时候能够连接,而且互相之间的对待是没有遗憾的。这种对待可以小小地从「岁寒三友」推出去,从「独善其身」到「兼善天下」这个值得投入的事业,最后活出一个值得为它而死的道理,他就很舒服了。
儒家经常有一个当时自我反省的意识,永远有一个可以意识到、甚至有没有意识到都一样的目的。为什么?孟子说「存心养性」,「心」是可以意识到的,「性」是意识不到的,但是当你存心的功夫作得好的时候,甚至当你没有意识到的时候,跟你意识到是一样的,这个就是「存心养性」。孟子是一个具有很严格逻辑能力的实践者,整个孟子的作品,从来没有带着意识使用「性」这个字眼,但是孟子使用「心」这个字眼,永远都在可意识这个地方来用,没有例外。你可以意识到的内容——「存心」,然后培养那个你意不意识到都一样的东西——「养性」。
所以就值得不值得而言,儒家的坐标是很特殊的。我们会在家天下这个地方检查这个「值得」,也会在公天下这个地方检查「值得」。如果从好的方面来讲,公天下的道德指标是一个提升,家天下的道德指标是一个落实;如果是从比较消极的方面来讲,家天下的活动是一个负担、是一个负债,使他没有办法很纯然地按照公天下的道德坐标完全地活动。所以积极来讲,公天下是一个提升,家天下是一个真真正正具体的落实。他的脑袋经常有一个公天下的指标的背景,可是他具体实践出来的道德,还是在家天下这个生活指标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在儒家里,公天下跟家天下的道德指标如果研究得深入一点,可以检证出不完全一样的东西。孔子是给它一个机会,在这个机会里面,希望带着家天下能够通向公天下。孔子认为只有一条路,就是教育,「有教无类」。就算家天下的人是一类、公天下的人是一类,只要有教育,将来家天下跟公天下的人之间的分界甚至都可以涂掉。这是一个思想家,在那么早的年代里面,他有一个公天下的向往、有一个家天下的落实、有一个人类成长的无可取代的教育制度,到现在看起来,人类愈成长,教育还是一条大路,没有问题。不管怎么讲沟通,不教育你怎么沟通,沟通有不有效跟教育的关系太大了。
有几个句子要特别提出:「反情和其志,比类成其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要讲细节的话,一个半小时讲不到三五百字。「反情和其志」是就个人来讲的,个人就是值得生活的人;「比类成其行」是从那个伴来讲。「比类」的意思是回到客观、回到人群来看一看,是不是能够这样作?是不是能够实践出来?所以「反情和其志」是一己之内,「比类成其行」是推己及人的事情,这两个就是儒家在进行它的值得不值得。看的颜色、听的音乐、思想的内容,或者是往来的时候的相处跟对待都一样,这个地方是儒家艺术很重要的地方。儒家还有一个信仰叫「顺生」,「使得耳目鼻口心之 皆由顺生」。「顺」是顺着的意思,「生」是发生的生。什么叫「顺生」呢?就是不会违背本来的那种好,「皆由顺生」。
再讲一个作为「乐」里面的核心的:「有司掌之,童子舞之,乐师辨乎声诗」,前面两个不重要,它前面说什么皇宫大礼,这个不重要,所以叫一个年轻的小孩按照这个节拍跟调子就可以;把很多东西摆好这也不重要,所以是任何一个司仪都可以管,可是乐师作为一个乐舞的灵魂人物,他只管一个事情,就是那个「辨乎声诗」,就实践来讲,就是他决定要怎么演奏。「辨乎声诗」的「辨」是一种深入的艺术批判。他面对这一个诗歌、面对这一场声音、面对这整个乐舞的作品,他有一种很深度的艺术上的批判,在他艺术上批判的时后做一个诠释,这个诠释就实现在他的指挥上。
我要说的是,在那个时候写这些文字的人,对于艺术的内心一点都不外行,他晓得前面这些没那么重要,所以请一些十四五岁的孩子动作起来会更好看;还有一些习惯礼仪、习惯当司仪的人,他们有一种很好的公务员的节奏,这个就是「有司者掌之」;而乐师真真正正是一个乐舞的灵魂人物,他对这一场声音跟这一些作为乐舞表达的文字,有一种艺术上精细的分辨:「辨乎声诗」,所以他的动作、他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接下来就讲到「德成而上、艺成而下;形成而先、事成而后」,就是指内在值不值得的那一份人格能够建立,建立值不值得的人格,才能够产生值不值得的作品,这个是很要命的。然后是「形成而先」,这个乐舞的先天是那位政治家的政治作为,基于这个政治家的政治作为给我们一个来源,才通过好多人的呼应,作为一个作品,这个叫做「事成而后」。「德成而上、艺成而下」,那一份值得的人格先成立了,才有值得的艺术。乐舞怎么来的呢?那个政治家就是这个样子,这样子的尧帝、舜帝,这样子的政治家武王「形成而先」,于是才有舜帝的乐舞、才有武王的乐舞,这个是「事成而后」。
现在我们碰到的是「事成而后」的那个「事」,我们碰到的是「艺成而下」的那个「艺」,于是就有了宋明理学最流行的这个字眼叫做「逆觉体证」。「逆觉体证」的祖先是「从用显体」,而「从用显体」的祖先就是《易经》里面的一句话:「是故易 逆数也」所谓「逆数」是说,我们碰到的是现象,但是我们追问一个现象如何可能,这是人类普遍的思路;就是说,这个事实摆设出来了,而使这个事实摆设出来如何可能?要问一个如何可能。
我们碰到的是乐舞,可是我们通过这个乐舞要追求的,是诞生乐舞的这个内在。所以当他真真正正在听的时候,他不是艺术的享受,他是人性的享受多过艺术的享受。这个是标准的儒家,因为他有个伴,他始终觉得这个东西对他来讲是好的、对人是好的,这就是有个伴。
有个伴的艺术家,不只是中国人,托尔斯泰就是。托尔思泰的艺术是感染论,就是说,好的艺术就是感染得深,这就是假定了一个伴,他从伴来开始考虑。这个伴可能是岁寒三友、可能是一乡一国,也可能是一天下,在乎感动的深浅、在乎感动的广狭,那一类的艺术就是所谓的「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他真正享受的,是穿过艺术的感动,领略到有这么一个值得认识的内心,这个这么值得认识的内心对儒家是很重要的。
就道家而言,你如果没有体会,当你面对现象的时候,那种浏览就不能到达道家所迷的「玄」;你没有一种幽深的玄,面对现象就没有办法作一种玄学的面对,当你没有办法作一种玄学的面对,你所面对的对象它的玄妙你就不知道。它的玄妙你不知道,你跟他谈,他就觉得你太浅了,可是那个玄妙是从他的肚皮里面来的。
「一箪食一瓢饮」也算有伴,那是「隐」的状态的伴。那小乘怎么转成大乘呢?其实我们说「小乘」是不应该的,如果小乘是自了,就没有小乘了。比如说,我叫很多人解决他自己,可是我还是教他们啊!那为什么还要转大乘?小乘跟大乘的区别,详细讲可以很丰富,简单说的话一句话。小乘的意思是说,你要警惕,因为烦恼有很大的障碍;大乘完全相反,大乘说,你应该高兴,因为烦恼有很大的力量。所以用减少生命能来修证的,他们就叫做声闻道;用加强生命能来修证的,他们叫作菩萨道。
儒家是使天下都能亲君仁民爱物,而佛则是使得天下都能入涅盘。法王的概念就不是入涅盘的概念,入涅盘应该是小乘的概念。法王的概念,是他那一种入涅盘的本性能够彻底的过渡,就是我可以让你都得道、我可以让天下人都得道,那就是法王。
还有一个概念是治理国家的,比如阿育王之类的,那个是人间的王,转轮圣王,那个概念是多出来的,不是原来大乘的概念,因为转轮圣王不出家的,但他还是在大乘概念,不过是落入显教来讲,就是说,我放弃成佛,但是我为世间的成佛增加好多机会,让在这个机会里面成佛的人越来越多。我放弃、但我增加机会,显教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显教跟密修最大的区别,就是显教从来都不须要了义的。显教的教主他本身是不究竟的,像智者大师他自己也没究竟的,但他为这个世间制造能够究竟的机会,他自己不需要究竟,他维持世间有这个机会,显教都不究竟的。我们站在密修的立场来讲,了义不了义是第一个要考虑的,圆教不圆教不重要,因为如果你自己不了义,你圆教还是不了的圆,不了的圆就不是佛法,但是显教在不了的那个场合里面制造很多机会。
讲回儒学,「尽心知性以知天」那个「知」是有意识的,但是落入有意识的那个「性」,就与「心」同断了。真正的「性」不是在意识上面讲的,这是在孟子的使用规律检证出来的,如果「知性」的「知」也落入意识来讲,那个性就不是纯悴的性,就等于说《中庸》讲的,那个刚刚冒出来一点点的,「诗曰:『德輶如毛』,毛犹有伦,『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无声无臭的「性」才是纯然的「性」,如果落入「知」,就还是「君子慎其独」的「独」。
刚冒出来的时后就是「莫见乎隐、莫显乎微」的时候、在那个隐跟微的时后、在那个不可知与可知中介的时候。「圣而不可知之谓神」,「性」在「圣」的一个不可知上,但是有它活动上的必然性,如果活动上没有「性」的必然,那就还是须要「存心养性」;活动上有其必然,就是孟子说的:「由人之行、非行仁也」,我不是按着仁义的班马线来走路的,而是我的步伐走出一个仁义的路,那是不通过意识跟通过意识是一样的。用我们的玩笑话来讲,那就是白老鼠。白老鼠每天都这样爬,因为牠已经习惯了,这个就是「随心所欲不逾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