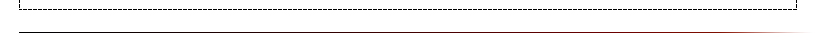何海霞刍议用墨
中国山水画是以墨为主,其实,在中古时期以前是以各种颜色为主的,直到魏晋以后,中国画受宗教的影响,特别是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开始把黑颜色——墨,当成主色。为什么呢?因为黑者,玄也,玄,就是道学思想,玄妙,玄想,是老、庄思想的反应,把世界五彩缤纷极其复杂的色彩提炼归纳到纯真——黑,这黑色里边所包容的内含十分丰富,再加上一个白,和黑与白之间的灰,就更是含蓄、深沉而莫测了。
上次我们谈了用笔。笔者形之骨也。那墨是什么呢?墨者,形之血也,形之神也。形象中的微妙变化,以及线所达不到的地方,就主要靠墨了。
常有人说:“某人似王洽泼墨,有人似李成惜墨。”我看也不过是说说。这“泼墨”和“惜墨”,不过是形象地告许我们:应当黑的地方我们就要非常珍惜这个黑,应当用它作为一种陪衬的时候,我们就尽量的泼。一聚一散,画龙而点睛。“李成惜墨”,李成买不到墨了吗?不是。李成画松针用焦墨,画树干用的是淡墨,这是一种传统的对比法,没有这焦墨,显不出那个淡墨来,如没有那淡墨,也就显不出那焦墨来。“惜墨如今”,就是用这一点墨,胜似你一大片的满涂,这就是点睛之墨。
中国画的吸引力,在于笔法和墨色,这是我们传统绘画中的可贵经验,梁楷画的人物的墨彩在那个时候达到了那个程度,是很不容易的;牧溪画狐狸,最后那焦墨画的胡子和漆黑的眼睛,猿猴满身的细密毛发,可最后细心用墨的地方仍然在眼睛上,他们就是用这几笔干线去征服观众,但我们现在有的画家就缺乏这个手段。
墨,有渴墨,有焦墨,有泼墨,种种,都是既出于偶然,也又出于必然,是任意而为之。笔是形之概括,墨是形之神,形之韵。有时看到一张画,虽然在形和结构上不够,还有毛病,但墨韵好,同样也能吸引人、打动人。我们说宾老80岁以后“善用宿墨”,是他砚台里就那么点墨。林风眠在藤黄里加墨,是他的特色,宾老善用宿墨,这是他的特色,信手涂抹,偶然天成。当然,也不能抓住这点,就说它是中国画的唯一方法。
墨色,有的是过滑,有的是过浮,有的是过于凝重。龚半千善于用笔,用墨还差点,我说他是笔胜于墨。他不以烘托为能事,而是以笔线为能事。有的人则善于烘托,如方方壶、石涛等一些方外人物,善于用墨,笔又不弱。
院体绘画的方法就是套色,像套色版画一样,一层套一层,一层套一层。笔的程序也是一层套一层,没有混脱入妙,这是宋画墨色的“风格”吧!院体绘画总的就是这样,在朝的都是这种画法,墨色非常单纯,轮廓勾出后,一层淡墨,又一层淡墨,突出焦墨,三层四层就够了。宋画之不足也,在于过份的程式化。宋代的绘画,特别是北宋,连款都不写,在画背后树缝里写着“李唐”,石头缝里写着“巨然”。到了元朝,墨色复杂了,混脱入妙了,任其自然,笔墨交融在一起,深浅浓淡,从心所欲。我是画宋画出身,由宋画又进到元画,元画的苍茫浑厚,是宋画之不及。有些文人逸士,那些真正的逸士、隐士,以书画寄情,用笔用墨散落,方外人、道家都是这样,赵松雪虽也称是道家,“松雪道人”,但不是真的,他是华贵的道家,他的出身不一样,他是二臣,赵子固与他,兄弟二人,是两个朝代、两个时代的人,赵子固是宋代,松雪归元代,兄弟到哥哥那里去,哥哥把门一关。我妄言之,赵孟頫的心情是沉重的,因为他得迎合元朝的皇帝。赵子固不是二臣,所以用笔、用墨都有高洁之感,很有气质,是一代名士。他们哥俩,一个淡薄一世,一个追求荣华富贵,是两个气质完全不同的人。
到了明代,文、沈、唐、仇四大家,既能文,也能画,属于士大夫阶层的绘画。到了晚期,又有一个变化,中国画的线是断断续续,含蓄着作者的心理和修养,我不是宣传董其昌,董其昌的画就达到了这个程度,八大山人不过得到董其昌的一笔就是了。董其昌的地位决定了当时的画风,一味追求笔韵墨彩,生活全失,没有真正发挥画家的胸怀,他的画路窄小。可在笔的运用上,明朝有大的突破,如青藤、白阳,有大的突破,同时有大的改革,那是一个创作自由的时期,寄情之画,画到就行了。到了清代,出了八家,还是文人画,水墨在他们手里是一个发展,肆意挥洒,抒发感情,但成不了大气候,因为他们的气质和胸怀,都只是自我。到了齐白石,注重对笔墨的玩味,既含蓄,又有深度,我认为是个发展。
关于淡墨和泼墨,我过去仅仅知道起一个淡墨、起一个中间调和的作用,淡墨更具有含蓄味。古人说:“人贵清明,画贵糊涂。”就是说:人要保持清醒的、理智的头脑,但在画画的时候,得要含蓄,得要模糊,得要有隐有显。这就给我们一些启发:画,不能画的太实,无中生有,有中变无,从有又到无,有那么点玄学之理。墨的变化,跟人的心灵变化一样,得要模糊,让人说“这人跟喝醉了似的”,其实没这事,脑子非常清楚而装傻。掌握了墨色的必然性,我必然有这个结果,那效果让人一看,嘿!偶然天成!其实是必然天成。可见掌握墨又用到这句话了:“惜墨如金”。有的人把“一得阁”墨汁成吨的买,而在所不惜,错了。用墨不是倾其多少的问题,而是用到恰如其分,这叫惜墨如金,把墨当成粪土似的往纸上糊,那是不懂得墨。龚半千的画大效果相当好,惜墨如金也在里边了。
积墨,积墨之法也就是堆砌之法,但不是唯一法。可以用积墨法,也可以用惜墨法,也可以用渴墨法,也许用湿笔法,这要看你反映的对象及你画时情绪等而定。就像你本来没有想画雨景,偶然天成出了雨景效果,就可以顺下去。
我们画山水的,不能意气行事,仅靠一时的激情那不成,一定要笔下有物、笔笔森严。这一笔下去的这一块墨,要做到天来之笔、墨韵非凡,就凭这点墨就让人鼓掌。我能做到这一点,我的那本册页,几笔过后,等墨润开来,不能再动了,保好。我用一笔墨画一把扇子,不蘸二回墨,恰到好处,艺术,不是让你把所有一切都交待得太清清楚楚,墨色的模糊之妙就也是画的魅力,画的魅力就是模糊,这主要是由墨色在起作用。
我们有的美术爱好者,对用墨不甚理解,往往有很多好的墨色最后给糊涂浆子了,不懂得惜墨和保墨,不懂救笔和救墨,一件本来失误的事,是可以败中取胜、转误为巧的,这在绘画上就是救笔、救墨与随机应变。
怎么保墨呢?我告诉你一个办法:发现这块墨画的好,放那儿凉着,干别的去,等他干透了以后,往上边略加点色,淡草绿、淡赭石都行,用色来巩固它。等色再干了以后,就怎么冲也冲不动它了、起到了保护作用。董其昌就用的是这个办法,笔精而墨妙,这也是一个手段。
画出一块好墨要把它好好的保下来,一张画就是凭这几笔叫座,凭这几笔征服观众。但要有几笔画坏了怎么办呢?人不会没有错的,画画没有不失误的,怎么办呢?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没完没了的在这块失误的地方打主意,你别管它,你在旁边认认真真的画好,就把它压下去了,这也跟打仗差不多,这个碉堡正面不好攻,你可以侧攻,还可以抄后路。这一块画坏了,你也别老在这打主意,转到别的地方、别的方法打主意,这里本来是线,线多而面少,就可以用面来补线,来救线。这块墨画的失误了,你赶快用水去拢它,别让它成了一块死墨,同时也是在旁边打主意,要看是面多还是线多,也许是以线治面,也许是以线治面。有人说:“怎么这么干呢?”不是干,是线多了。“怎么老和泥呢?”是线少了。还有,湿的时候你还老往上加,没有不和泥的。
画画,不是非得“三日一山、五日一水”的,也不是非得每天老老实实地画够八个小时,重要的是要善于用笔、用墨,善于保笔、保墨,还要学会善于救笔、救墨。
前面提到泼墨,这“泼墨”可不是个动词,而是当形容词来用的,大胆下笔加上细心收拾这才谓之泼。落墨之前,是有构思的,心里凝重、沉着、认真,落墨之后要随自然的变化而变化,要加工,好的要保,失误的要救,要细心收拾。无意识的、散发情绪式的泼,那是一勇之夫干的事。
笔墨的运用,如同作战,要有战术,要有计划、有步骤,还要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因物(工具)而异,因势而异。既要保笔带笔、保墨带墨,又要救笔带笔、救墨带墨。掌握了这些,就得心应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