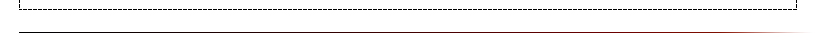造假奇人
陈巨来
汤临泽
汤临泽(安),浙江嘉兴人。少时曾为药店学徒,因羡慕秀水文后山、曹山彦、张子祥、潘雅声诸名家之刻印作画,故即弃其所业,而从事刻印作画矣。渠善临摹名家印刻,精心研究,后得明文衡山犀角章二方,遂异想天开,专收破旧明代犀角杯等(因渠曾为药店学徒,当年药店所用犀角,均如此收购也),改制成亭云、三桥、文水道人、祝枝山、唐伯虎、沈石田等,凡能在珂版画册中见到者,无一不照样刻成,其底之平之深,叹为观止,而虫蛆、裂纹,尤为逼真;印底所存旧迹朱泥,虽以水泡数日亦不脱也。(此法,及假造宋元旧象牙印古色斑烂之方法,悉以授给余矣。说穿,至平常也。)所成几达八十方,悉以售诸平湖藏刻面印大家葛书徵(名昌楹)。葛公自诩古缘独深,尝遍请丁辅之、高野侯、赵叔师、褚松窗等至其新闸路家中赏鉴,诸公无不赞美不止。时为壬戌、癸亥间也。余侍叔师同诣葛家,获睹放在两红木大盘内,真是古色古香。葛君特点示十余方外间从未见过的文衡山名号,葛云:此当年文氏后人珍藏在一锡匣之中埋于地中者,近有人连锡匣一并携来,故为新发现之珍物云云。葛氏二年之中,前后所费已逾三千金矣。当时葛应丁、高之嘱以最佳罗纹纸,上绘纽式,下钤原印,名曰《明人……印谱》(名已忘,大概如此也),售作二十元一部云,似六册。后来什么仇十洲、金俊明、方孝儒,层出不穷,陆续到了葛氏书斋求售,纽亦粗糙不精了,遂启葛氏之疑,拒而不收矣。汤见已拆穿作伪情况了,遂少作少卖了。时余年十九,已与之相识矣,渠已近五轶矣。渠尝招余至其家中自述其事,家在当时之拉都路兴顺里,两宅一楼一底,一宅为其居家,一宅乃做假字画之工场也。渠一时高兴,偕至工场间一看,为一裱画间,只一工友。天井墙壁上什么文天祥条幅、史可法对联、祝枝山等等等等,几十纸均雨打日晒,无一完整者矣。余呆了,问之曰:破得如此,有何用处呀?汤笑云:要他破损不堪后,再取下修修补补,方能像真的了,可以骗人上当嘛。又告余云:渠曾在嘉兴张叔未后人处以二元买得清仪阁残拓片一包,包的纸头为一二尺之旧皮纸,尚是张翁亲手所包者,于粘口处亲自写“嘉庆某年某月叔未封”九个字。写包处,适在左下角,吾遂拆开将“封”字撕去,写阔笔墨荷一幅,撕去角上,钤一点点假廷济印于上,卖给了姚虞琴,得价二百元也。姚君得后大喜,求吴缶老题字。缶老竟只认叔未亲笔,以为作画绝品超品也,遂为长题诗句于上。汤氏笑谓余曰:这画,吾做得还有一些露马脚地方,因为这纸自嘉庆年折至现在,折痕无论如何去不掉了,如果细心研究,书画哪有用包东西的折法收藏,西洋镜立即拆穿了。次年姚老又以该画出示于叔师,余适在傍一观,果有折痕也。当时余绝不说穿,窃笑而已。有一次,余随汤同至城隍庙冷店中觅小玩意,见有一长方板旧牙章,上刻“子孙保之”白文浅刻四字,汤以四元买之。隔半年后,以原印出示,已变为“文天祥印”四字朱文了,深底,积朱至旧。汤谓余曰:吾费力刻了,竟无人收买,仍以四元卖给你白相相罢。余谓之曰:何必急急,终有一天会有人买去的。他识为对的。不久又来赠余胡卢(葫芦)小印犀角质者一方,曰:此印本伪作“十洲”二字,因无人请教,故磨去改刻你名字相送了。在敌伪时期龚怀希辑瞻麓斋古印谱成,余见后附有宋女道士“鱼玄机”三字白文玉印(亦汤所作)、文天祥印牙章二方。余询龚老以多少钱买得?龚云:二印一共为二百银元,价至廉也,云云。余为之窃笑不止。
丁丑、戊寅间,一日,湖帆忽谓余曰:汤临泽做假货,今日吾始五体投地矣。余询其故,吴氏云:去年汤来向吾借去明人陈(或程)鸣远精制紫砂茶壶一个,说明要翻砂仿制的。隔了四个多月,把壶还吾了,同时以仿制者出示于吾,但一看是新壶耳,亦不以为意。昨天汤又来了,出仿制者见示,已一变为明人气息矣。汤请再出示原壶对较尚有不足之处否,及吾取下一比,竟一般无二也,两壶盖交换盖之,亦丝毫不爽。湖帆云:如不亲自看到,两盖竟不能分别也。汤笑云:吴先生,你放心,壶底上吾已换了另一名家之名矣。吴云:作伪至此,叹观止矣。
后忽闻其得奇疾,虽在六月亦需盖厚被,用四个“汤婆子”暖其周身,不可见风,一见风,即大颤不已云。约有十年之久。(一九)六三年病重,入第六人民医院,不治身死了。尸身已放入太平间矣,半夜汤忽苏醒了,大呼吾没有死呀。放出归家,其病若失,遂照旧访亲觅友了。(一九)六四年余在掮客钱镜塘家中又遇见了,一别近廿年,相见甚欢。余询以当年葛氏所藏之十余方文衡山印何故崭新?汤云:以前所制犀角印,都以明人破犀角杯廉价得之,故做假易,后得一犀角,为一现代物,做假包浆殊不易,故只能穷想方法,做一锡匣子分三行,行四格,每印放入后,用锡合口,再加以化学涂之,埋入泥中。锡本易黑,上加药物,一年多即变成古气盎然了。再剪开作为新出土古物了。葛氏受了蒙骗,以一千元买去的。后来吾印章不做了,专收罗无款识的古金彝器,假添文字,文字完全在名器物上东集西凑,略减篆意,而用松香等等涂上刻以欺人的。容庚辑的《金文篇》上即有许多字是吾改造而成的云云。钱镜塘即取一商爵示之曰:这件是你所添的铭文吗?汤云:巧得很,是的。钱云:你提证据来。汤云:可当场拆穿给你们看看。遂取一火柴点着了,汤说:只能离开二三分熏之于旁,如铭文上得热气,即发出松香味来,那即是伪添的了;如火太近,字即烊了。真铭文尽烧不妨的,云云。是年余已六十,汤八十余矣。汤忽对余云:你元朱文名望很大呀。余曰:哪有你的古拙像真呀!汤竟云:不妨不妨,吾来教教你。余因其老了,故只能对之曰:请教请教。他竟说:只要买一部王虚舟所写篆文《四书》,用以仿写刻之,即包你像了。余曰:吾六十了,这书也没有,算了。汤云:吾代你买。余云:吾《四书》已久忘了,要寻字,太难了。汤云:那容易,只要买一部《十三经索引》,一查即得,吾也代你买。余云:太不敢当了,你如此高龄,千万不必了。他连说不妨不妨。余只能一笑而别了。隔只三天,钱镜塘忽以电话至画院,谓余曰:汤老已将二书代你买到了,王虚舟篆文《论语》,四本,四元,《十三经索引》一册,十元,一共十四元,吾已代你将款付与汤了,你来取书罢。余无法,即去付款取书了。心有不甘,次日即去四马路古籍书店,询问此二书有否、价若干?服务工作人员谓余曰:有二部,前五天已被汤临泽买去了。余问价若干。答云王石印四册一元、《十三经索引》三元也。一转手间十元赚去了。余念其老,无可奈何,只能一笑了之。回家后立即以王四册给了学生、《十三经索引》给了左高矣。(一九)六五年汤真逝世矣。身后殊萧条,所有遗物变卖殆尽,尚存破旧未制成品之牙章六方,无人收受,其学生陶冷月之子也,携来求余以十元为求受主。余仍念其昔年之情,故即为介绍于龚仲十元收购矣。又据湖帆云:汤尝以破旧宋纸回炉重造,制成竟与宋纸一般无二,惜只能制成尺页大小而已。
周龙昌
周龙昌,仅知为杭州人。昔年在上海开设裱画装池店(店名亦失传),以善补古画出名者。民初上海寓公南浔富翁嘉业堂藏书家刘翰怡先生得恽南田花卉尺页一册,已蛀蚀不堪,召周询之曰:能潢治否?周答:需半年,保证整旧如新。刘愿由其开价,但须住在家中潢治。周因可得任其开价,故即住至刘宅,半年未出刘氏之门。及裱好呈于翰翁过目。翰翁大怒,谓周私自调包。周力辩无此事,全为用技术修补而成者。刘不问情况,即送周至当时巡捕房,严加审讯。及查明无事,已关了数天之久了。周受此大辱后,心灰意懒,竟将店闭歇了。时张大千方以专造伪石涛、八大、石、姜实节等等用以绐取当时沪上四大豪富之一程霖生(源铨)之巨款。(程昔年所居,即今上海静安区公安分局也。)程所藏石涛、石、八大四五百幅之多,大千伪笔居十之六七也。张氏昆仲知周已不开店了,遂以每月二百银元聘之至家中,另租一宅,专由周氏为之装裱,一年二三件而已。至抗战后,携之同去成都,专为修补旧画,每月增为三百元了。据大千告余云:此人挖补工夫,已至神出鬼没程度,任何破碎,任何人物、山石、亭子等等,均可搬东迁西,无丝毫破绽可寻也。尝有一次有人以一手卷,绢本,元人五百罗汉白描像嘱裱,裱好后即取去了。又隔二年,原主又在某古玩店见一十八罗汉像绢本小卷一件,画者变为另一元人矣。原主睹此,颇似自己所藏五百尊者中之像,乃回家启视已藏之卷,是否为人取偷临摹的。首先发觉降龙、伏虎二尊失足了,乃从头检点,竟只存四百八十二像了。再仔细详看,又一无痕迹可寻,绢又一无损伤之形,遂发奋以巨值购进此十八尊小卷,所织之绢又经纬分明,一无剪补之形。明知一分为二,已不能合二为一了。为之徒唤奈何而已。胜利第二年,周氏随大千回沪了。余在李宅曾与晤面。余见其年已六十余,一诚笃老人已。其时余方以湖帆己卯所画九方扇面临摹玄宰墨笔山水一页示之,为亡三弟之款。余意欲求大千反面亦画几笔,以出售贴补寡弟媳。大千一见大赏,谓可混作董画,允作立幅一帧对调(后此画以百元售去)。次日大千以扇示之周氏,二人相商如何挖补。大千云:这亭子似太挤。周云:可以搬至左上角也云云。余在傍亲见此事也。后余与周渐熟了,问其罗汉卷子事。周笑云:这是四十岁以前的事了,现在目光不好了,不能再做了。余问之,纸头可拼拼补补,绢一丝丝的,如何做法。周云:绢反比纸易做,因纸质各各不同,要找完全相同的,方可补修。绢,元明大都相同,挖补不易看出来的。余又问曰:绢,一丝一丝织起来,太不易了罢。周云:只要心细,纤维对正,织成原样即可了。余问:用何工具?周云:一竹丝签,一极薄象牙片子即可了。
郑竹友
郑竹友(筠),广东人,出身未详,仅知其为一能画之掮客而已。据人云:他与扬州画家许徵白(昭)为二人合作造假古画以为生活者。(一九)五五年时,郑尝奉当时英商汇丰银行华总经理李广剑之命,嘱余刻印,因之相识。郑氏于造假画事,殊不讳言,据其自云:创作非其所能,只要有一真本,渠可临摹,一丝不走样的。据其告余云:原与刘定之为老搭档,刘裱画,凡有需修补者,必郑为之。后二人成死对头,为金钱也。郑云:(一九)五三年刘定之以三百元收得石涛山水一幅,原有长题三百余字,惜被火烧去几二百字。幸该画未损时曾有有正书局珂版印本,刘求郑代补这文字,许以出卖后除去本钱,所赚以四成赠郑。郑为补好后,刘出售,只付以三百元,云仅赚七百元云。后一年被郑查到买主谓以一千八百元收进者,郑知只得二成。又:刘定之尝接得文徵明尺页,嘱裱生意,内有一页为红墨水所染污,刘逾漂逾坏,竟不成画了,亦郑即取原尺页素白对页一纸,为之复制一页,天衣无缝。刘亦只给少许之款。有此二事,郑与刘遂绝交了。郑本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一九)六二年余回申后,始知已由北京故宫博物院聘之至北京故宫专司修补古画工作矣,月薪近二百元云。此人与汤、周相较,技似稍次,而收获胜于前二人也。
补记二人
上述汤、周、郑三人技术后,又忆及二事,用补述如下:
二裱工均属于扬州派,据刘定之(定之为苏北句容人,但其技术属苏州派)告余云:苏、扬二派,迥然不同。苏州派擅精装,纸、绢画虽数百年不损也,但漂洗灰暗纸绢,及修补割裂等技均远逊于扬帮。扬帮能一经潢治,洁白如新,但不及百年,画面或如粉屑,或均烂损不堪矣。故湖帆自藏之书画,均刘定之所裱,如得元、明、清名家破损灰黑色之画将以出售得巨价者,必交一马老五(名未知)者装裱之。
马老五,扬州老裱工也,丙寅、丁卯间开装池店,名“聚星斋”,设在今铜仁路慈厚南沿马路,时杭州高野侯丈居处即在慈厚南里七二六号,出弄口即马店也。高所藏五百本画梅及数百楹联,均马一人所裱者。丙寅余介湖帆与高丈相识后,高即以马老五推荐于湖帆矣。似戊辰年,湖帆以廉价购得明书法家詹景凤一丈长、二尺四五寸高,横卷一幅,字作大草书,大者每字几五寸。湖帆招马氏出示之,询能否割裂改制成四尺条幅,四幅、六幅,均不拘的。马云:可以代制,但价需一百五十元云。湖帆允之。隔了数月,居然改成条幅(几幅已忘)。是日余适在吴宅,目睹每条虽向日光映之,亦无痕迹可得也。湖帆遂将全文诵读一过,忽笑谓马氏云:马老板,你出了烂污哉。随指第二幅第一行末一个“宀”与第二行第一字“元”字,告之云,这是一个“完”字呀,被你腰斩了。马云:这“宀”与上一字一笔连下来的,与“元”字离开三分之多,吾不识草书,故有此错误,一准重做可也。说毕即取去了。后半年余询湖帆,这“完”字已完成否,吴云:宀已转入第二行,连着的一笔,亦一无破绽是剪断者云云。后高丈被匪所绑,即回杭州后,马亦关店了,大约回乡矣。
胡某,亦一扬州老裱工也,设“清秘阁”装池于威海卫路,成都路石门路之间,时已在抗战时期矣。先君常以书画嘱裱,成为友人,取费至廉矣。老人生二子,长子(名已忘)传其技,老人死后,仍为店主。次子名若思,为张善子、大千昆仲弟子也,今尚在画院中为画师,画甚佳,但品行至不堪,张门逆徒也。抗战时,尝伪造大千画数十件,在沪开张大千“遗作”展览会,皇皇登广告,被大千所见,遂亦登报,曰“小子鸣鼓而攻之”。其兄与余亦至熟,尝见店门上写一牌,收购宋、元、明、清死者喜神,尽破,破得只剩下半身亦要的,当时所收几达一二千张。余问何用?胡云:吾收到旧画,需要修修补补者,即取出喜神,各代纸张选一同型者补之也。喜神,人家祖宗神像也,无人所要的,故几角也可买进了。又:渠告余云:灰黑古画,必须向浴室大汤洗剩之肥皂水,买来后,将画浸入历若干日(几天他守秘了)取出,重漂之,即灰暗全去了。又:修补古画时,将同型旧纸,最注意将纹路对准,以锋利刀作不规则划之,如是破者去,整者丝毫不爽填补进去了,不规则,错乱人自光,不及注意耳。其人早死,店亦关了。以浴水漂画,据云,人身油污,亦正利用之也。是非余所知矣。
选自 陈巨来《安持人物琐忆》